踏莎行·院落深沉
[作者] 洪邁 [朝代] 宋代
院落深沉,池塘寂靜。簾鉤卷上梨花影。寶箏拈得雁難尋,篆香消盡山空冷。釵鳳斜欹,鬢蟬不整。殘紅立褪慵看鏡。杜鵑啼月一聲聲,等閒又是三春盡。
《踏莎行·院落深沉》賞析
藝術之妙,在於曲中達意。即使那些被人們推崇為最善於“直抒胸臆”的作者,也總不能全如日常口語那樣直接、質樸地表達。這叫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。清人袁枚《與韓紹真書》云:“貴直者人也,貴曲者文也。天上有文曲星,無文直星。木之直者無文,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;水之靜者無文,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。”因而,司空圖的“不著一字,盡得風流”(《詩品》)便被公認為文學作品最高境界之一種。洪邁這闋《踏莎行》寫思婦懷人,通篇沒有一個字點破本題。作者的本意沒有直接表達出來,完全是通過環境、氣氛,以及主人公的動用、情態顯現出來的,因此算得上一首善達言外之意的極品。開頭兩句的“院落”、“池塘”乃是女主人的生活環境,而這環境的特點是“深沉”與“寂靜”,一上來就透露了境中人的孤單與寂寞。第三句寫到“簾鉤”這獨轉換使讀者加深了冷清空闊的感覺。一般人表達孤寂都用“簾幕低垂”等句。但這往采自明刊本《詩餘畫譜》往缺乏效果,洪邁卻別出心裁,煉出“簾鉤卷上梨花影”一句。試想:簾鉤卷上也只有“犁花影”前來作伴的生活,是多么的空虛和寂寞?以上三句著力渲染環境。那么人在何處呢?她在彈箏:“寶箏拈得雁難尋”。她在出神地望著燒盡的篆香:“篆香消盡山空冷”。“雁”字連“箏”字說是指箏面上承弦的柱,參差斜列如雁行,稱“雁柱”。柱可左右移動,以調節音高。呂渭老《薄倖》詞:“盡無言、閒品秦箏,淚滿參差雁。”而這裡的女主人公卻是“寶箏拈得”而“雁難尋”,連音調也調試不準,有相思而無法於弦抗訴說,眼看著“篆香消盡”而懶得去添,以致帷冷屏寒,其難以入睡也可知矣。“山”是畫屏上的山,如牛嶠《菩薩蠻》所說的“畫屏山幾重”。這一句所寫的情境,《花間集》中頗多見,如歐陽炯《鳳樓春》“羅幌香冷粉屏空”,毛熙震《木蘭花》“金帶冷,畫屏幽,寶帳慵熏蘭麝薄”,張泌《河傳》“錦屏香冷無睡,被頭多少淚”,都可作為理解此句的參考。女主人公這一整夜都是在淒涼中度過,那么以後的日子呢?又將“守著窗兒,獨自怎生得黑”呢?過片的“釵鳳”三句寫主人公容貌。“釵鳳斜攲”、“鬢蟬不整”、“慵看鏡”,形象地反映了受痛苦煎熬相思成災的樣人。這使我們想起了《詩經·伯兮》中的句子:“自伯之東,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,誰適為容。”以及徐幹《室思》里的話:“自君之出矣,明鏡暗不治。思君如流水,無有窮已時。”“杜鵑啼月一聲聲”,表面上只寫環境,只是在進一步創造冷清的氣氛,因為“杜鵑啼血猿哀鳴”是自然界最悽厲的聲音么!實際上這裡還用催歸的杜鵑表現思婦對行人的期待。前面已經說過,上半闋的結句是在暗示一夜將盡,到下半闋的結句則說“等閒又是三春盡”。讀者試想:詞中所著力描寫的一夜,已經令人俯首欲泣,那么一月,一年,數年的光陰將如何熬得下去呢?講到這裡,我們不得不佩服句中那個極平凡的“又”字用得是何等神奇!洪邁的《踏莎行》特別注意引尋、啟發讀者參與到詞中意境來。我們剛一接觸到它,只能感知到一片空寂的環境和一個慵倦的主人;等到鑑賞進一步深入,我們才發現這是一個思婦對丈夫的深切懷念;如果你有興趣再追下去,那么還可以想到關於愛情、離別等更多的東西。正如梁啓超所說:“向來寫情感的,多半是以含蓄蘊藉為原則,像那彈琴的弦外之音,像吃橄欖的那點回甘味兒,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樂道的。”洪邁此詞就是具有“弦外之音”極品。
《踏莎行·院落深沉》作者洪邁簡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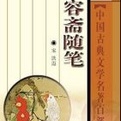
洪邁(1123——1202),南宋饒州鄱陽(今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)人,字景盧,號容齋,洪皓第三子。南宋著名文學家。